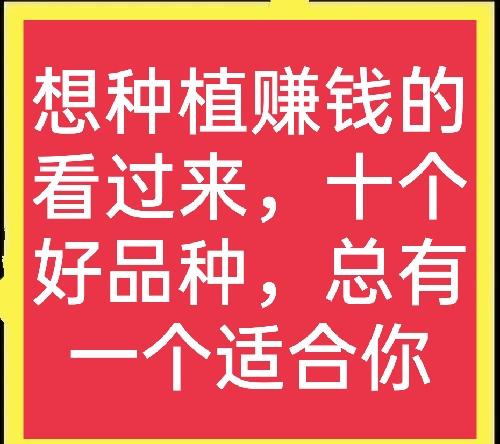美人去后空余床
/ /
《长相思》
(唐)李白
美人在时花满堂,美人去后空余床。
床中绣被卷不寝,至今三载犹闻香。
香亦竟不灭,人亦竟不来。
相思黄叶落,白露湿青苔。
/ /
家中诸物,与身体联系最紧密的,莫过于床。诞于斯,哭于斯,作乐于斯,薨于斯。一生从床上开始,在床上结束。世界再大,也大不过一张床。再怎么不平凡的人,一躺上床,也就整个儿平凡了。
当然,这是指身体的维度,在三次元体验中,身体无疑是我们最重要的依恃。记忆的种类纷繁,以身体的记忆最为持久,身体记忆之中,又属嗅觉记忆最为深入。
试想当爱人离去,家里看上去一切如常,但同时又很不一样,其中最异样的就是那张床。你独自躺在上面,感觉它如此空旷,好像一片废墟,而你的身体如一个遗址,飘满往昔的记忆。
不论古今,不论中外,人与床的关系,以及身体记忆,皆大同小异。李白此诗,以直观的生命体验,图解了这个全人类亘古的公共隐私。
《长相思》,一题为《寄远》,《全唐诗》将其与另外两首闺情诗编在一起,题为《杂曲歌辞·长相思三首》。美人,指所欢,所恋之人。“美人在时花满堂,美人去后空余床。”太白的乐府诗,即使不配乐,我们也能听见那音乐,跌宕抑扬,低回反复,诗句本身就是乐句。这两句极美,美人在时,满堂生辉,时光如花绽放,美人去后,空余床。
花满堂与空余床,形成巨大对比,一满一空,自不必说。且说室内家具应该都在,并非只剩下床,但感觉却是空的,空气中的明朗和芳香,也尽随美人的离去而消陨,只有那张床,仍是一个现场。
“床中绣被卷不寝,至今三载犹闻香。”床上的被子,自美人走后,便卷起来不再盖,至今已三年,还能闻到美人的余香。人对气味的记忆,对某些气味的迷恋,有时是安慰,有时是个谜。
“香亦竟不灭,人亦竟不来。”此二“竟”字,惆怅至极。要如何是好呢?这样的相思,“相思黄叶落,白露湿青苔。”如果说黄叶是韶华凋零,白露是点点泪珠,青苔便是无声的荒芜。美好又寂寞,浩盛而悲凉,也许这就是爱情。
明 林良《灌木集禽图》(局部)
气味的残留,早晨的咖啡
李白的诗情和意象是古典的,生命体验却直通现代。美国诗人詹姆斯·泽摩尔曼有一首《思想之空旷》,与太白诗异曲同工,我们来对比阅读:
这个早晨我感觉
如果你死了,我的生命将怎样
床变得广阔无边
鸟儿仍旧在鸣唱
气味的残留
早晨的咖啡
思想的空旷
我心中震耳欲聋的寂静
相信这位美国诗人并未读过李白的《长相思》,即使碰巧读过,他们所写的仍是两首不同的诗,至少长相和气质完全不同。美人,花满堂,绣被,以及“相思黄叶落,白露湿青苔”这样的句式,都是现代诗不会有的。反之亦然,早晨的咖啡,以及“我心中震耳欲聋的寂静”,也不可能出现在古典诗中。不是规定,你可以写,比如把咖啡写进古体诗,但那感觉会很怪异,就好像给古代仕女戴上一副近视眼镜。
也就是说,古典诗有古人生活中的事物,有古人的感知和表达方式,而现代诗来自现代人的生活体验,有现代人的语言和表达方式。这是很自然的事,古今各有其美感。
这首现代诗采用日常的说话方式,同样有惊心动魄之感,诗的开始:“这个早晨,我感觉/如果你死了,我的生命将怎样”,谁没有过这样的时刻?晨光熹微中,当你看见枕边人朦胧的侧影,会有那么一瞬间你突然想到死亡。
第二三小节,两个句子之间相互映照,“床变得广阔无边/鸟儿依旧在鸣唱”,鸟儿的鸣唱是从床的空旷中听见的,又使床变得更加空旷。“气味的残留/早晨的咖啡”,气味与气味的交谈,气味对气味的悼念。
异曲同工之处在于,不论借用什么事物,不论以哪种方式表达,真正的诗,其核心永远是诗,它超越时代和社会制度。正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所言,一首纯粹的诗,必定是最现代也最古老的,最感性也最绝对的,最日常也最超越的。
在《思想之空旷》一诗中,作为核心的诗,与李白的《长相思》并无二致。也是写爱人离开后,自身独处空房的感觉,最异样的首先也是床,“床变得广阔无边”。李白写的“空余床”,实际上也有这个意味,那张突兀的、被空出来的床。
其次是气味,隐秘的记忆,无形的生命。“气味的残留”,不止床上,家里处处都会残留那人的气味。还有咖啡,咖啡的气味氤氲着早晨的温馨,而如果你离去或死去,早晨还是会喝咖啡,但那将变成不同的滋味。
两首诗的最后,都写世界的空旷。“相思黄叶落,白露湿青苔”,横向铺开时间的荒芜;“思想的空旷/我心中震耳欲聋的寂静”,纵向展现存在的虚无。
南宋 马麟《暮雪寒禽图》
那张无法解释的床
我的妻子带着她的衣服消失了。
她落下两只尼龙长袜,以及
一把掉在床背后的梳刷。
我想吁请你的注意
看看这些苗条的长袜,看看
梳刷齿间光泽的黑发。
我把长袜丢进了垃圾桶;梳刷
我留下来自己用。只有床
看上去奇怪而无法解释。
以上是美国诗人雷蒙德·卡佛的一首诗,题为《我的妻子》。这不是正常的离别,也不是想象中的缺在,而是突然的断裂,一个突发事件:妻子离家出走了。
理解这一切需要更多时间,一个通宵,接下来的几天,或许几个月。诗所捕获的是发现妻子消失后的瞬间,那个被放大并拉长了的瞬间:惊愕,乃至有些麻木。他检视着家里,就像看图A和图B有什么不同,我们也跟随他的视线看到了重要细节。
衣服肯定被带走了,通常女人离去,最先空出来的都是衣柜。她留下了什么?两只尼龙长袜,没说一双,而说两只,这是用搜寻的眼光在看,两只长袜被孤零零地留下,仍是一对,它们的形状勾勒出她双腿的线条。还有梳刷,因掉在床背后而被落下,上面有她的头发。
这些私生活细节,具体而亲切,闻着长袜和梳刷的气味,他简直可以把她找回来。但他没有,似乎很冷静地,他把长袜丢进了垃圾桶,梳刷留下来自己用,请注意,这是在诗人吁请我们注意那长袜和头发之后。我想,诗人是在以调侃式的冷静,克制着内心涌动的感情。
只有床,最后他的目光定格在床上,那床看上去很奇怪,怎么个奇怪?诗人没有说,而是说无法解释。想起卡佛的短篇小说《为什么不跳个舞呢?》,那个中年男子在自家门口出售家具,其中就有一张大床和一个电视机,一对年轻情侣对之很感兴趣,随后男子痛快地接受了还价,还请他们喝酒,并播放唱片,提议他们为何不跳个舞呢。
卡佛的诗和小说,多聚焦于普通人,当日常生活被某个事件打乱时,他们会感到惊讶和异样,察觉到事件背后更多的东西,但由于不善言辞且从未学会和内心交流,因此往往陷入“无法言传”的困境,而作者也拒绝提供解释,一切任由读者自己去补充。